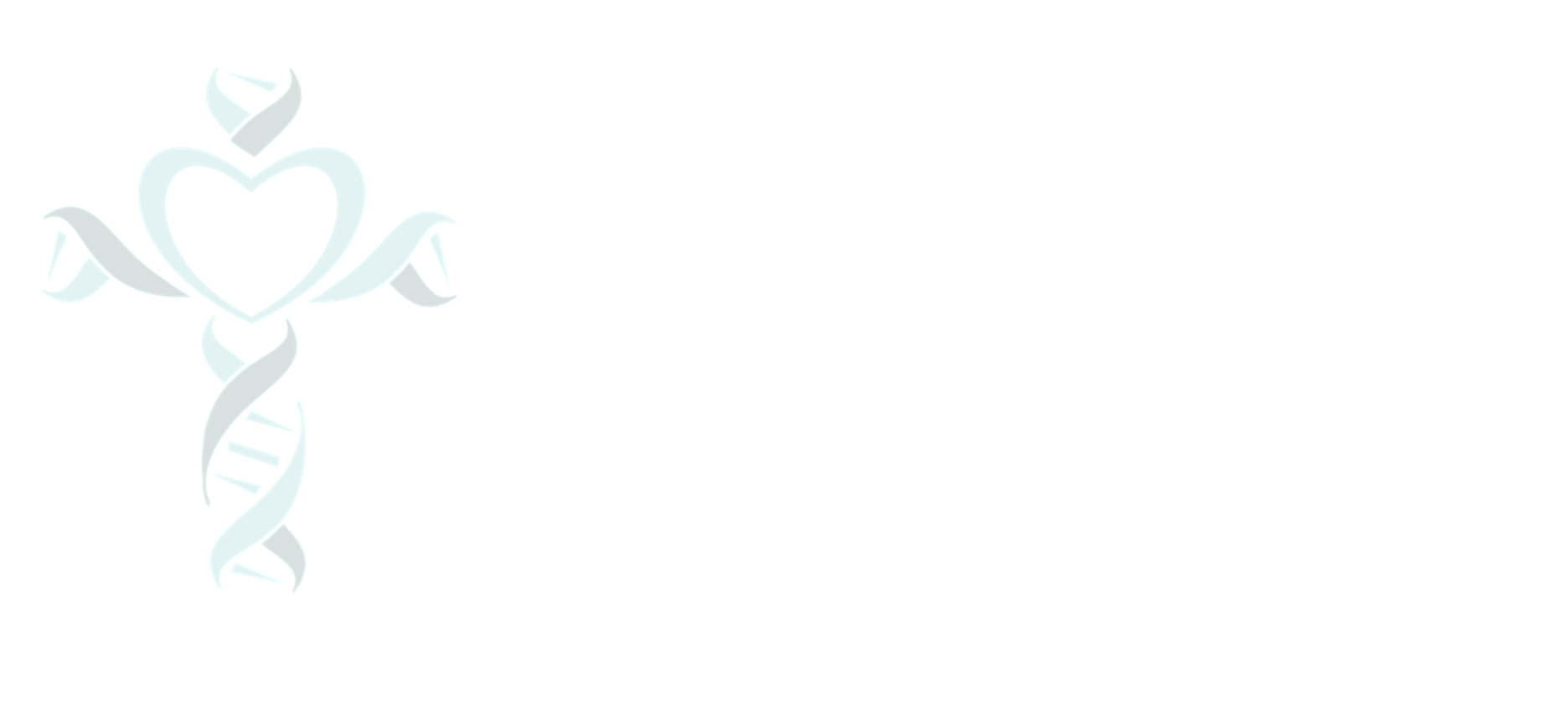
小時候住台中時,郭大夫(Dr. Don Nicholls),是我們全家人的醫生。從小我就非常喜歡這位親切的外國醫生,他看起來從來都不忙,總願意停下來和你多說一兩句話,帶著慈祥的微笑,給人非常溫暖的感覺。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盲腸炎需要開刀,那時大概才國小二年級,當護士把我的衣褲脫掉消毒手術部位的皮膚之後,叫我不可以摸消毒的地方就離開了。我只是個八歲小朋友躺在手術台上,看著房頂的大手術燈,陸續有穿綠衣戴口罩的工作人員進出忙著準備器械。當時的我感到很困窘又緊張,因為自己無助地躺在陌生的地方又沒穿褲子。這時郭大夫也經過,看了我一眼,臉上還是熟悉的微笑,他一句話也沒說,走過來用消毒巾幫我把下半身蓋上,又走出去了。他身為醫療團隊的主管壓力責任最大,竟也是唯一注意到一個小朋友未說出的心理需要的人,這是我直到如今仍感激在心的往事。手術前他慣例地帶我們虔誠禱告,然後幫我注射麻醉藥,之後我就在平安的心情與完全的信任中昏睡了。 小時的印象留下的不多,但我記得的還有幾件事,其一是每次去郭大夫的靈光診所都看到成堆的腳架放在一個走道上,因為他收容了許多小兒麻痺症患者來做復健。另外是他故意使用兩個診間來看診,所以每次看完一個病人可以有一點走路的運動到另一診間去,病人的隱私也更受到尊重。他也保持著幽默感與病患說話,媽媽說有一次她因喉痛看診,郭大夫詳細檢查後很正經地說「這個疾病婦女比較多」,她很認真聽著,郭大夫寫完病例,抬頭笑笑接著說「因為她們說話比較多」,這才知道是開玩笑。 但小朋友去靈光診所最怕的事是驗血,幾乎每次感冒發燒都要到檢驗室用一根針扎在指頭上,再擠出一滴血給檢驗室阿姨放在顯微鏡下檢查。有一次我因害怕堅持不肯扎血,結果郭大夫也放了我一馬。當時感冒發燒所開的 aspirin 藥瓶完全是英文的,現在才知道那叫做原廠藥,價格貴很多。我大約五年級時頸邊摸到幾個軟軟的淋巴粒,直徑約有指甲大小,郭大夫幫我局部麻醉,一邊取出一邊問我會不會痛,我聽著切割與刀剪、金屬盤的聲音,因心理作用又害怕就說還會痛,他又加注射了一些麻藥。手術之後他給我看取下的四個放在藥水中的肉色的檢體,他告訴爸爸說要送到彰基做病理化驗,因為靈光診所無此設備。我因好奇向他要檢體,他仍微笑,後來取了一個小的放在小瓶給我帶回家。這種高水準的醫療在近四十年前是不計成本的,事實上後來我才知道靈光診所低廉的收費使他們年年虧損,完全是靠國外奉獻才能維持營運。 郭大夫說的話不多,只有在禮拜天會出去主領佈道或崇拜,但他所自然流露的基督徒的生命卻給患者如陽光般溫暖與安慰。醫學倫理不應只是理論與開會,而更是在真正醫病關懷的實踐中,也唯有從耶穌來的活水能使一個離鄉背景數十年,又日夜忙碌照顧病患身心需要的醫生,活出像郭大夫這樣精采而令人難忘的生命來。 數十年後我也成了醫師,為了追尋心目中典範的前輩我好幾年四處打聽郭大夫的消息。幾經巡訪後發現他還健在,已八十多高齡,目前於澳大利亞的一個宣教學院中繼續培訓下一代的接棒人才,並且每年都設法回台灣一次看看他的孩子們(當年的七十幾個小兒麻痺症患者現在都已長大)。他們彼此想念,也都期待每年一度的團圓。去年利用他回國時終於找到他,並且與這位深深影響我,所尊敬愛戴的前輩醫者合影留念,願上帝繼續賜福給他的僕人,讓他的一生成就上帝的榮耀,成為更多人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