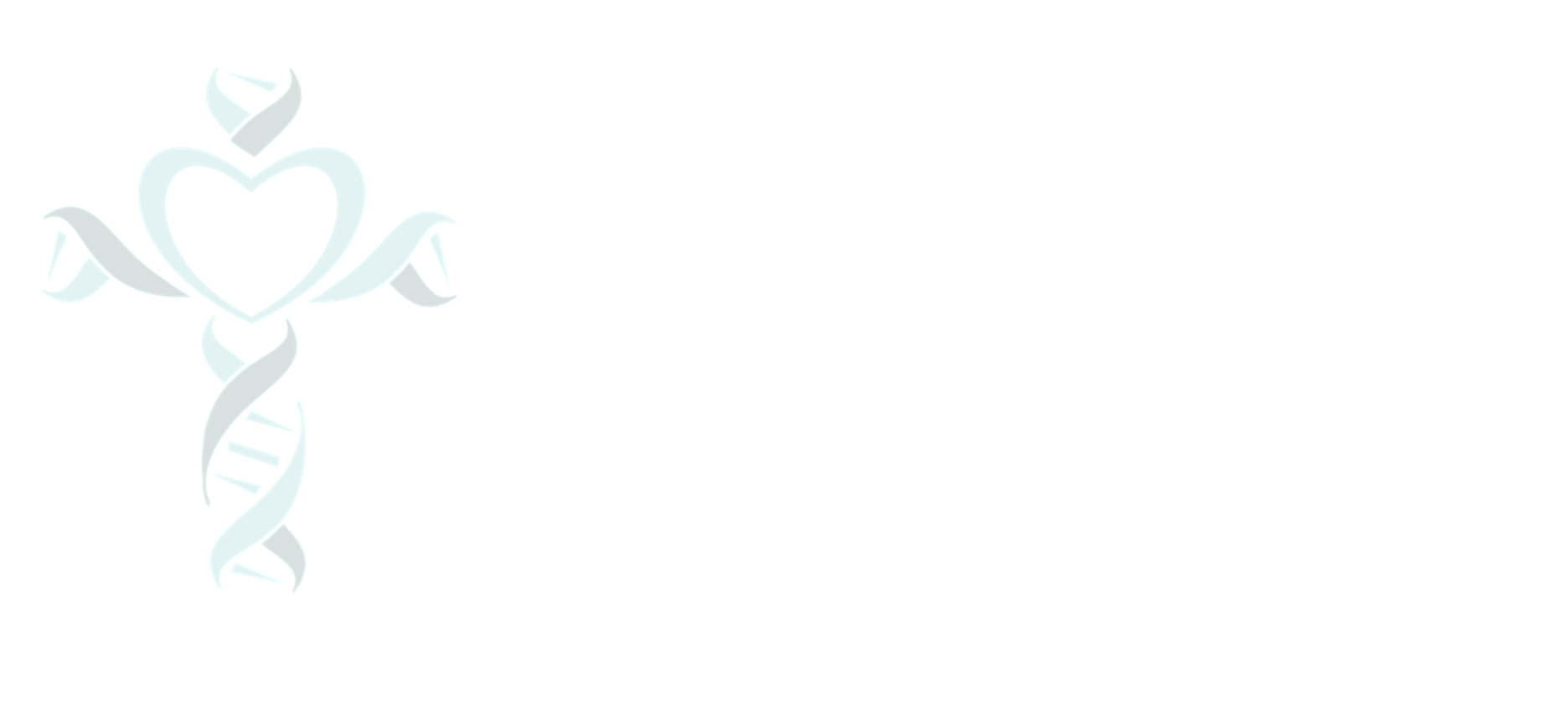
**一、前言**
在風聲鶴唳的納粹時代,德國大部分基督徒都對希特勒的恐怖統治噤若寒蟬,對當時德國政治宗教界將希特勒拱為基督的代表也都沉默不言,但1934年由巴特 (Karl Barth) 起草的「巴門宣言」公開勇敢地反對時代潮流,指出唯有基督是上帝惟一之道,所有與這惟一之道悖離的都是誤謬的,這種在白色恐怖中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引起我的注意,因為筆者相信只有知行合一的信仰才能有這樣大的勇敢。之後在閱讀當中發現巴特在非基督徒當中,尤其是在共產主義背景的中國大陸宗教哲學界也有不少讀者,其中思想最頂尖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更是出了好幾本有關巴特的研究與書評,更有趣的是,巴特在瑞士一個不到兩千居民的沙芬維小村(Safenwil)當牧師的時期曾經熱心參與社會主義運動,成立工會,但後來卻離開了社會主義的路線。
在二戰結束後,巴特對於兩大陣營的冷戰十分關注,他批評西歐缺少對東歐人民的同情,甚至指出反對共產主義在原則上比共產主義更罪惡[1]。巴特也批評西歐沒有設身處地站在俄羅斯的歷史處境作考慮[2]。他因為這些獨排眾議而偏左的觀點受到不少批評,這樣的背景使他更加與眾不同,我想或許其思想轉變的歷程與社會主義背景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會有對話的機會。像他這樣的人為何會離棄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他如何看待曾經熱心的社會主義運動?因此探討巴特早期政治觀,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的觀念轉變是本文的探討動機。
**二、歷史背景**
2.1.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與瑞士(1914- 1918)
這是一場主要發生在歐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戰,約死了一千萬人,主要是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戰爭。德、奧、義是同盟國,英、法、俄和塞爾維亞是協約國。德國戰敗後簽署屈辱的「凡爾賽條約」,失去了13%的國土和12%的人口,並被迫解除武力[3]。當時瑞士雖保持中立,但是公民仍被征入伍防衛,而且戰時德語區和法語區之間已存的對立更加尖銳,分別支持不同的陣營。
2.2. 納粹德國
一戰戰敗重創德國的政治經濟,國民對當時的威瑪共和失去信心。那時納粹黨領袖希特勒於1933年上台,以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再度激起德國人的熱情與對光榮歷史的自信,他宣稱德國的困境之根源來自於屈辱的「凡爾賽條約」、懦弱的威瑪共和國以及握有國家經濟命脈的猶太人,又在德國境內強勢取締共產黨,受到越來越多德國人的支持,使納粹黨成為國會內第一大黨,開始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當時德國基督徒受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對希特勒的執政充滿期望,因此當時「德國福音教會」內一面倒擁護納粹政權。後來一群親納粹的德國信義會基督徒成立「德國基督教」(Deutsche Christen),成為日後希特勒統一及操控全國基督教團體的政治工具[4]。希特勒實行優生與種族滅絕政策,在德國及其佔領國領土上建造死亡集中營,約600萬猶太人與七萬德國殘障人士與5000殘障嬰兒被屠殺。
2.3.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與瑞士(1939-1945)
從1939年納粹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下入侵波蘭開始,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以美、蘇、中、英等國組成的同盟國與以德,日,義等組成的軸心國交戰。全球有有19億以上的人口被捲入戰爭,死了六千多萬人,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5]。如同亞洲的日本,德國起先勢如破竹,但在戰爭末期卻節節敗退,1945年蘇聯紅軍攻佔柏林,希特勒最後躲在總理府地堡裡自殺。瑞士政府在二戰中試圖保持中立,因此曾拒絕了上千的猶太難民入境而遭國際批評。然而在瑞士民間很多教會和組織都積極地支援難民。
2.4. 認信教會與巴門宣言
「德國基督教」成為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傀儡後,選了一個親納粹的人Ludwig Muller為國家主教,並通過「亞利安條款」以排斥猶太血統牧師。這段時期,「德國基督教」不斷地對全國各地的教會製造「希特勒與基督的相似性」,例如:「希特勒為了我們而奮鬥,藉著他的權柄、他的誠實、他的信仰和理想,今日救主已經來臨了」。後來甘脆主張希特勒是德國的彌賽亞,鼓吹基督教與國家社會主義結合,主張丟棄《舊約聖經》、否定保羅神學等。這時許多德國基督徒才開始發覺不對,但在當時舉國狂熱,又到處是秘密警察的政治環境中,大多數人都選擇沉默以自保,加上德國信義宗政教分離的傳統,使希特勒對猶太人的逼迫有恃無恐。這時一些勇敢的基督徒如潘霍華等開始成立「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人簽名,但是當權的教會主教們卻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1934年巴特起草著名的巴門宣言(die Barmer Erklärung),強調教會只能效忠基督,拒絕接受別的主之錯謬教義。此宣言的小冊隨即傳遍整個德國,銷量達二萬五千本[6]。但總體來說,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仍屬於少數群體。
**三、巴特個人簡史**
巴特於1886年誕生於瑞士巴賽(Basel)的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中,其父為改革宗教會牧師及巴塞神學院的教師。1904年巴特開始在瑞士伯恩大學讀神學,1906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之後又到德國杜賓根及馬堡大學就讀,追隨幾位當時著名的自由神學教授如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等人。
巴特在1909年按牧,奉派往日內瓦德語改革宗教會工作,在實際的牧會與講道中,他開始發現自由主義神學的局限性,因為他的會友多半是低階層的工農,主日講道時面對會眾他發現這些自由主義神學對渴慕的心靈毫無用處。在幾年的鄉村牧師生活中,巴特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而他一方面牧會,一方面也熱心參與瑞士宗教社會運動,非常關心社會民主工人運動的發展。這段鄉村牧會期間他也寫了第一版羅馬書注釋,於戰後1919年出版。當時他才卅二歲,在著述中強烈批判自由神學的人本誤謬,沒想到竟像丟了一枚震撼彈引起熱烈討論,也招致許多敵人,他形容自己「像個在黑暗中爬上教堂鐘樓的人,想要攀住欄杆,卻抓到了鐘繩,拉響了激蕩全鎮的警鐘」[7],因著這本書使他在1921年受邀至德國哥亭根大學任教。
由於巴特在德國求學期間所景仰的老師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都簽名支持德王戰爭,使他質疑批判這些自由派神學家的倫理立場[8]。巴特發現整個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根源來自士萊馬赫[9]。由於自由神學建基於人的經驗,對人類的前途過於樂觀,卻未能在戰爭中分辨危機,巴特開始覺得聖經不應只是人對神的觀點,相反應是神對人的宣示[10]。他從自由派夢想中覺醒後力挽狂瀾,成為當時抵擋自由神學最重要的主將之一,使許多自由派旗下的神學生與學者回歸真道。
1934年希特勒才上台一年,敏銳的巴特就已經起草〈巴門宣言〉,提醒教會不要盲目追隨「德國基督教」團體,他持續反對納粹的言論並協助猶太人,拒絕在上課前行希特勒的敬禮,也拒絕當時規定效忠希特勒的宣誓程序[11],結果在第二年就被納粹政府驅逐出境。回到瑞士巴賽爾大學教書這段期間,巴特陸續出版了《教會教義學》系列巨著,直到1962年退休時,其著作已影響了整個歐洲的神學思想,被視為「新正統」神學的代表。巴特一生最後幾年,每週還定時不斷地到監獄去講道,於1968年辭世,享年82歲。
**四、巴特早期對社會主義的立場**
巴特對有關社會主義的著述相對較少,因筆者語言能力有限,所以搜尋的範圍僅限於中英文資料。根據歐力仁的整理,巴特在瑞士沙芬維村(Safenwil)牧會時期(1911-1916)是極端政治性的(radically political)[12],當時年僅25歲的他不但充滿牧會熱忱,而且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巴特經常到工會發表演說,內容多為社會主義和耶穌的教導之相關性,強調社會主義就是要讓耶穌在福音書中的教導具體落實在世界上[13]。他不僅在當地開課教育工人爭取自身權益,更積極地呼籲工人籌組工會來抗衡資產階級。1911 年巴特在工會中發表〈耶穌基督與社會運動〉,宣稱「耶穌就是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就是當代的耶穌」[14]。他看出中產階級的教會文化對窮人的社會需求採取莫不關心的態度完全違反基督的教訓,因為耶穌親自進入社會與窮人站在一起,所以耶穌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終極的目標。他深信上帝國離窮人比較近,因為他不但領導而且親身參與「社會運動」[15]。1914年,巴特在一篇以〈福音與社會主義〉為題目的講章中強調,「社會主義的訴求是實踐福音的一個重要的因素」[16]。有錢人要進上帝的國是如同駱駝穿過針眼般地不可能。巴特在1950年回憶錄中說,「當時瑞士的年輕牧師,…全都成了廣義或狹義的宗教社會主義者。我們激烈地反對布爾喬亞[17],(我們對於要反對的比對於要贊成的知道得更清楚)。」
在牧養窮人與弱勢者的會友期間,他看出自由神學中的資本主義色彩,與對人類前途光明美好的錯誤假象,加上哈納克老師支持德皇一戰的錯誤,對自由神學失望之餘,他漸漸把對人性的希望轉到對社會運動,他在演講「宗教與社會主義」中提到:「我從未發現有什麼地方的金錢比人民更重要,有什麼地方可以繼續以財產來作為一切價值的標準,有哪一個地方一方面強調祖國比人性更重要,另一方面卻又不讓人民處於焦慮和卑賤之中,有哪一個地方的人愈來愈覺得現在比未來更有希望。因為社會主義超越這些思考方式,所以儘管它有不少缺點......,對我而言它是最令人振奮的記號之一」[18]。因此1915 年一次大戰中他加入瑞士社會民主黨,被親切地稱呼為「牧師同志」(Comrade Pastor)或「沙芬維的紅色牧師」(the Red Pastor of Safenwil)[19]。他給好友Eduard Thurneysen的信中說「每主日我的証道都只談一些末世的事,我無法再容許自己處於當今邪惡的世界中卻像浮雲般飄遊,相反地現在就應該證明對至大者(上帝)的信仰並非屏除,而是涵納未完成領域的工作與苦難」[20]。1917年沙芬維村有55位女工因試圖籌組工會而被工廠老闆威脅遣散,巴特牧師見義勇為親自出馬去與工廠老闆談判,巴特自稱像是「摩西對法老」說話一般,而老闆也遭逢「畢生最難纏的對手」,因沒想到除了對付女工,竟還要對付她們的牧師,最後因巴特的協助而工會未遭解散[21],但該牧職的不易是因為該村也有許多會友不喜歡牧師涉入太多的政治活動。
**五、巴特對共產革命與社會主義的洞悉與覺醒**
但是在1919年德國唐巴賀(Tambach)一場研討會中,約100位瑞士與德國的宗教社會主義領袖面前,巴特卻首次公開主張上帝國與在場所有宗教社會運動者的努力無關,他說「上帝國並非始於我們的抗議活動,而是在一切革命之前的革命,也是一切現存秩序之前的秩序。[22]」因此上帝一方面對現存秩序說「不」,另一面也對革命者說「不」,巴特要他們小心不要把基督世俗化成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的領袖。同年他在另一場演講中題到對蘇聯十月革命的失望[23],他說這樣的革命雖是必要的,但卻不應模仿。因為巴特在此革命中看到幾個問題:首先暴力手段使革命者未脫離舊秩序的根基,其次無產階級專政只是製造了新階級而並未消除階級,第三仍是少數人執政,並未解決民主制度的問題[24]。巴特的諍言影響了瑞士社會民主黨後來決定不效法有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使少數支持蘇聯第三國際的會員憤而退黨另組瑞士共產黨,其中包括巴特好友Fritz Lieb教授[25]。其實在這之前,當鄰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s)未反對德皇發動戰爭時,巴特已對鄰國的宗教社會主義者失望過了[26],他於1915年曾說「宗教社會主義等事已過去,開始對上帝之事認真對待[27]」,但當時可能他對瑞士的社會民主黨仍抱著一絲希望。不料在1916年又發生一件事,使卅歲的他開始從社會運動的政治熱忱中醒悟過來,當時沙芬維村的工廠大老闆為了收買人心而藉機大批宴請巴特的部分會友,沒想到這些人竟甘願拋棄原有的理想,立刻被政敵的宴飲收買了,這一個事件讓巴特深深地體會到,政治的意識形態並不能搖撼人類根深蒂固的罪性[28]。人的思想是搖擺不定的,是易受影響的,加上在實際牧會時,他發現不論是自由神學或是社會主義,這種種的人本理論在面對人心最底層的幽暗面時顯得極度虛弱而無力,他覺悟到教會的講壇不應該是宣導政治理念的演講台,而應是宣揚《聖經》信息的地方。從此以後,他不願再積極地從事政治活動,並開始把注意力回轉到聖經本身,幾個月後(1916年6月)便開始潛心寫作,共花了兩年多時間完成著名的「羅馬書注釋」。
在該書十三章注釋中巴特用一個神性的大負號來否定一切以人為中心所試圖建立上帝理想國度的努力。巴特說:「若將現存的秩序如國家、教會、權會、社會、家庭等等的總體設為
(a+b+c+d),
將上帝的本原秩序對這總體的揚棄設為括號前的負號:
-(+a+b+c+d),
那麼顯然,革命作為歷史行為即使再徹底,也不能視為在括號前對人類秩序的總體實行全面揚棄的神性負號,而是充其量只能視為這樣一種可能成功的嘗試:揚棄括號內的現存秩序作為現存秩序擁有的人性正號。於是得出以下公式:
-(-a-b-c-d)。
在這一公式中必須注意,括號前巨大的神性負號很快就會出乎我們意料地將括號內,人擅自以革命方式搶先改設的負號重新變成正號。換言之,鑒於神人之間的局面,舊事物經革命的算法在崩潰之後會以新的形式捲土重來,而且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29]。這種「革命者本身也需要被革命」的公式可謂對人類政治史一針見血的描述,因為結果會變成「反叛者通過反叛站在了現存事物的一邊」,因為巴特透過聖經的智慧,看出在本質上,革命其實是「惡與惡之間的鬥爭」[30],在所有人的本性裏無法逃脫的罪性使高呼正義的革命者失去了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雖然帶著「不」字的革命者因對現存秩序的挑戰與為公義的奮鬥而更加接近上帝[31],但也因此使他更加危險,因為他自己有自義的危機,支持者也都有誤將革命者當做基督一般地追隨與高舉,而變成新的盲點。巴特說革命者心裏想的是一種理想,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如對罪惡的赦免與死者的復活,但實際上幹的確是另一種革命,是可能的可能性,是不滿、仇恨、抗拒、暴動和破壞[32]。「最大的義,乃最大的不義」[33]。所以只有讓基督掌權,人保持謙卑順服上帝的態度,才有機會脫離以惡報惡,冤冤相報的循環,效法耶穌「以善勝惡」的足跡。
這一時期的巴特,雖然繼續關心窮人與社會公義的實現,卻已發現革命也一樣不能帶人脫離嘆息勞苦的不義社會,因此他從熱心的社會運動中覺醒退出,主張政教分離,這對基督徒而言像是一種消極的、防守型的政治哲學,意味著不發怒,不推翻,但也不妥協,不迎合的政治態度。只將倫理的希望放放在一種更高的權柄上,而不冀望在政治國家的當權者或革命者身上。巴特轉而勸告昔日社會主義革命夥伴們勿把未來的世俗政治盼望,投射到耶穌基督所要建立的終末性的上帝國本身,以免讓上帝的神聖國淪為另一個有名無實的世俗國度。
巴特在1906年認識布魯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後者曾擔任瑞士社會民主黨副主席,是傑出的基督徒政治家。布魯姆哈特提到羅馬書8:22「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因此受造的世界本身不可能是上帝國本身[34],這樣的觀點給巴特很特別的啟發。巴特說:「布魯姆哈特所做的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做不到的。他描述上帝來世界的目的,卻不挑起世界的戰爭。愛世界,也對上帝完全地忠實。與世界同受苦並為世人的需要仗義執言,同時也強調世界需要等待外力的拯救。不僅把世界引領到上帝的面前,也把上帝介紹給世界;不僅在上帝面前為世人辯護,也扮演將上帝的和平帶給世人的使者。不斷地、堅定地向上帝祈求「願您的國降臨!」,並且與人一同等待、催促上帝國的到來」[35]。因為布魯姆哈特以純正的信仰態度面對上帝,所以才能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去關心社會議題。更重要的是,布魯姆哈特相信只有上帝的主動,而非人的努力,才能達到上帝國的臨到[36],因此他不像其他的宗教社會主義者那般急躁進行各種行動,反而是以耐心與心平氣和的態度來等候上帝主動出手[37]。巴特發現,從上帝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式的上帝國對人民而言是弊遠大於利,因為它讓人有「愈來愈不需要真正的上帝國」之幻覺。在建構一個社會主義式的上帝國之過程中,「我們的行動阻礙了上帝的行動,我們的理想遮掩了上帝的理想,我們生活上的富足妨礙了寧靜的靈命之成長」[38]。其次,他指出,當真正的上帝國降臨時,一切人為標準下的對立--敬虔與不敬虔的、道德與不道德、聰明和愚蠢......等等--都將因為被上帝的標準取代而消失。正如「當太陽升至最高點,陽光普照全地時,高山與峽谷之間的差別就顯得毫無意義了。」因為上帝國擁有改變所有價值體系的力量。因此,人類社會的改革絕不是促使上帝國來臨的充分或必要條件。「夜裏所點著的燈終究是人為的光,無法與破曉的陽光相提並論」[39]。人類視為「善」的行為唯有出於上帝、符合上帝的標準,亦即「在上帝國裏為基督而做的善」,才能稱為真正的善。真正的「公義、和平與喜樂」是上帝國來臨後所賦予人的「上帝/基督中心」自律性,而非人類企圖用來建立上帝國所發展出的「人類中心」[40]。
然而,若因此以為巴特的政治態度自從離開社會運動就轉趨消極,則是個錯誤的印象。他之所以主張政教分離,是要革命者警覺到自己永遠不是救世主,所要建立的理想也永遠不是上帝之國,革命者因自己的罪性與當權者一樣,所以必須謙卑儆醒,以免自義自大,反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但對他而言,沒有政治層面的神學是不可能的,因為基督掌權於全世界所有的角落,包含實踐的政治與倫理的領域,所以一個順從上帝之道的基督徒必然對政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41]。他雖然在教會教義學等神學性著作中不再談政治,但他說「我所有的神學都含有政治層面,不論是明示或暗示。我的羅馬書註釋於一戰結束時1919年出版,雖然內容論及政治的不多,但卻有政治影響力[42]」。他的生活也繼續實踐政治的關懷。在二戰初期(1933年) 的潘霍華,因反對希特勒與「德國基督教」而受到強大的政治與人際壓力,所以離開德國來到倫敦考慮接受一個德語教會的牧職缺,但他感到孤單、恐懼與迷惘,就寫信給他的老師巴特說「我不懂為何我的思想與朋友們極端地對立。我的看法逐漸孤立,雖然我同這些朋友們仍走得很近。這情形使我恐懼,我的信心也開始動搖,或許教義讓我走偏了。因為我不覺得自己的思想會比和其他牧師朋友們更好或更正確,尤其是其中有些非常優秀的牧師是我真心尊敬的。」,巴特回信說「若你問我的意見,我會用最強的火力斬釘截鐵地告訴你,…立刻回到你在柏林的崗位上![43]」,這正代表他的政治立場:一種順服上帝的堅毅、智慧與影響力,不再是忙著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國,卻是不可忽視的、讓作官掌權者如芒刺在背的洞察與不妥協,一種與被欺壓者站在一起要求公義的聲音,一枝強權威嚇不了的筆,這是基督教的「無為」[44]:接受上帝對自己的否定,因為祂也正用一個巨大的否定指向眼前不公義的政府。
1935年巴特被納粹驅逐趕回瑞士後發現,相對於德國教會因反納粹所遭受到的壓迫和苦難,瑞士的教會卻對納粹的暴政保持沉默,寧願投入所謂的「道德重整運動」而無視於鄰國弟兄姊妹的痛苦[45]。巴特對瑞士基督徒這種自私的想法大加批判,並不斷地與瑞士各區教會領袖公開辯論。他認為瑞士基督徒的漠然態度是瑞士教會史上一段「讓人羞愧得不願再想起的時期」[46]。二戰開始後,巴特不但大聲呼籲瑞士全國要「不計代價地」在思想上和軍事上反抗希特勒的侵略,更親自加入武裝的國民兵以行動保衛祖國[47]。由於巴特不斷公開譴責瑞士政府拒絕猶太難民入境,甚至遣返已逃入境的難民,讓懼怕激怒德國的瑞士政府十分頭痛,不但禁止他公開演講,甚至違法監聽錄音他的電話[48]。他也寫信給捷克和荷蘭的神學界朋友鼓勵他們武裝抵抗納粹德國的侵略[49]。
二戰後進入東西冷戰對峙時期,在當時西方社會這樣一個全面反共的年代,他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極不留情,又與鐵幕下的教會領袖、神學家保持密切的關係,例如在1948年應邀前往匈牙利,巴特非常同情匈牙利教會在共產政權底下的處境,認為不能以西歐人的觀點評價東歐教會的取向[50]。他也呼籲東西歐教會應捐棄彼此意識形態的成見,為了「耶穌基督的團體」而共同尋找出「第三條道路」來建立一個自由的世界[51]。當時巴特這種同情東歐人民,批評西歐的立場,備受各方非議。當蘇聯鎮壓匈牙利的反抗時,巴特面臨很大壓力加入反共宣傳的政治陣營,但他仍不靠邊站,反而認為「共產主義已經在匈牙利受到判決了,不需要我們這邊的判決[52]」。卜仁爾(Emil Brunner)因此質疑同樣是面對獨裁者,為何巴特對希特勒如此堅決地拒絕,但是對史達林如此寬容[53]?巴特說「我們不應把共產主義與十年前(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提並論,後者無論在意義或動機上都是愚不可及、瘋狂的罪犯。但馬克思主義[54]與第三國際[55]的意識形態在任何一刻都是不同的,史達林也與希特勒等人不同。蘇聯所處理的問題,雖然因污手沾滿了血腥而讓我們義憤填膺,但畢竟是個建設性的主張,試圖解決我們這邊一樣有的嚴重而急迫的社會問題,是我們乾淨的手未曾以同樣的熱誠解決過的。只要還有一天我們有西方的「自由」來製造經濟危機,…而人民仍繼續在挨餓,至少我們基督徒就應該拒絕對東歐說出嚴峻的『不』[56]」。他並非支持史達林的獨裁,而是像耶穌一樣,要西方民主陣營在拿起石頭要丟擲行淫婦人時,先反省自己心中同樣的罪。他說不論「馬克思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帝國、和法西斯主義者,耶穌都為他們死」[57]。
在這許多特立獨行的言談中,其實我們可以看見巴特擁有一顆極為關心貧乏弱勢者的心,畢竟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至少在馬克斯的理論上是站在窮人這一邊的,馬克斯的確是想解決人類一個實在而嚴重的問題,但納粹主義卻是發揮達爾文進化論的優勝劣敗到極致,以致逼迫殘害無助軟弱的殘障者。戰後他還常不忘提醒德國基督徒,他們在縱容「納粹德國」與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事上有無可逃避的責任。他強調德國教會是甘心樂意地投入「反社會主義」與保守勢力的陣營中的,此舉的結果便是導致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掘起,他清楚的頭腦與堅持使他一直不受時代主流的歡迎,甚至受到多方攻擊,但也讓我們看出他的基督教式的無為是什麼意思。
**六、結語**
巴特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他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目睹法國社會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的興起,經歷希特勒的時期,也見到了東西冷戰的對峙。但他在一戰時因老師支持德王戰爭而從自由神學夢想中覺醒,也因教會會友被商人收買而看出社會主義的革命理想只不過是一種罪人攻打罪人,以惡報惡的實際,不可能根本解決社會公義的問題,因為核心的問題正是羅馬書中明示的人性的罪性與敗壞。在這思想不斷突破與亮光中,我認為巴特是非常有智慧的,他雖曾被誤導但卻有不斷反省改革自己的習慣,此即「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58]。田立克(Paul Tillich)儘管與巴特的立場不同,並對他提出不少的批判,他仍說「巴特的偉大,在於他注視境況並依境況以反覆不斷地修正己論,辛勤地力阻自己成為自己的追隨者。[59]」這樣願意隨時受教修正自己的思想,也符合他的神學,即上帝是至高無上的,而有限的人在上帝與其透過耶穌基督所啟示的真理面前,只有謙卑聆聽與順服的可能,如他在教會教義學中所言「作為一個儘管有罪,卻在基督之中得以稱義和成聖的人,信仰、服從和懺告耶穌基督,他就做著對人合適的自然的事情,因此也在真理之中」[60]。
如同「違逆潮流」( Ever Against the Stream)[61]的書名所示,巴特的洞見使他總被視為是個違反潮流的麻煩人物。清醒的頭腦,獨立的思考,使他無法與時代中檯面上的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的大人物坑燦一氣。但是巴特又是一個「能夠超出其時代情境的思想家,他總是能從「遙遠的」思想先驅那裡(如保羅、安瑟倫、馬丁路德、加爾文、杜斯妥也夫斯基、祈克果、莫扎特等)獲得一種新的眼光來打量自己的時代,看出自己時代的「不正常」,並試圖為克服這種不正常而尋找藥方」[62]。我個人雖不認同巴特神學的啟示論對聖經的立場,但對他的種種抉擇包括離開自由神學、譴責德國兩次大戰的發動、批判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西方的盲點,我卻打心底衷心佩服。他因對「社會主義式上帝國」的批判造成昔日同志的不滿,因對自由神學的攻擊而被迫與昔日的老師公開爭辯[63],因起草巴門宣言而被納粹趕出德國,甚至回到瑞士後都因他對納粹的批判及協助猶太人而被政府警告[64],最後在他的追思禮拜中,以他在國際的知名度與學術地位,卻沒有一個瑞士政府官員參加,可見他的言行並不受作官的當權者歡迎,如同許多先知型的人物一樣。
從對革命的熱情到透過聖經與聖靈的光照,對人性黑暗面的洞悉,拋棄了自由神學與共產主義中對人性善良面過度樂觀的誤認,也反映出巴特超越時代的遠見。從歷史上我們看到法國大革命中革命者的殘酷不下於被革命的皇宮貴族,蘇聯十月革命的史達林,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文革,柬埔寨共產黨波帕的大屠殺,每個事件都不是無緣無故,而是假借信念、進步、革命之名進行的,革命者最終都陷入當初理想熱情中被革命者無法逃脫的、根深蒂固在人性最深層的腐敗與罪性,完全如聖經羅馬書七章所啟示的一樣,人的理想審判人的行為,人的行為也審判人的理想,唯有至高至聖的上帝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審判者。巴特反對一切試圖與上帝同等的意識型態或主義[65],這也正是廿世紀許多出於同情弱勢族群動機的激進革命的思想如拉美的解放神學、北美的黑人神學、女性主義神學、或韓國的民眾神學等所需注意的盲點;也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許多試圖將「實現上帝國」等同於「台灣加入聯合國」時,濫用聖經名詞來背書自己意識形態的盲點。這使我想起曾在戒嚴時期遭政治迫害的舅舅陳映真,他是台灣極少數的左翼文學家,也因思想超越時代潮流而一生踽踽獨行。在他散文集「父親」裏題到他所尊敬的基督徒父親,也就是我的外公見他醉心於社會主義時,對他充滿智慧的勸誡:「父親說他皈向基督以後,才認識了人原有的罪性。而這人的罪性如果沒有解決,終竟會朽壞了人出於最善良願望的解放和正義的運動」[66]。
今天台灣的國會委員們與媒體以高度自義的姿勢批判別人的時候,正落入了巴特所指出的陷阱當中,當一群罪人在指責另一群罪人的時候,耶穌的話是最好的回答:「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67]。今天弊案纏身的陳水扁前總統,當年不正是正義與揭弊的化身嗎?當年文革批鬥別人的紅衛兵今天也反成了被歷史批判的對象。誠如巴特所言,人與人所建立的一切政權都是負面的,唯有先接受上帝對他的否定,人類才有真正的出路,上帝國才有實現的可能,這是基督教式的無為,否則不論是什麼主義,理想的幻滅是必然的結局,無論是革命者或是當權者,上帝的審判仍將無情地臨到一切自以為義的人。
然而我們也應該避免另一極端,就是如同二戰時期德國與瑞士基督徒一般地對猶太難民見死不救,這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教會也是個令人羞愧的事實,巴特說「一個沉默的團體,只有袖手旁觀的團體,不能算是基督徒團體[68]」。我們看見巴特牧師勇敢地幫助沙芬維女工,冒險幫助猶太難民,譴責武力侵略的強權,鼓勵潘霍華與東西歐許多神學領袖,化解冷戰對立的誤解,這除了需要智慧,需要愛,更需要勇氣。台灣內部的國語教會和台語教會,海峽兩岸的教會,大陸內部的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之間,其中不也糾結了多年的歷史愛恨與意識形態情結嗎?我們何時能學習高瞻遠矚的巴特,看透時代的盲點,不以自己為義,成為使人和睦的上帝之子[69]呢?
[1]The Vernard Eller Collection,Christian Anarchy Chapter 5, Karl Barth, Theology of Christian Anarchy,http://www.hccentral.com/eller12/part5.html
[2]Karl Barth, How I Changed My Mind. Edinburgh: The Saint Andrew Press, 1966, p. 63。
[3]維基百科,第一次世界大戰,http://zh.wikipedia.org/
[4]維基百科,第三帝國的崛起,http://zh.wikipedia.org/
[5]維基百科,第二次世界大戰,http://zh.wikipedia.org/
[6]郭燕歡,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網上中文基督教資源中心,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096.htm,瀏覽日期為5/26/2006。
[7]張纓,歷史,還是啟示--哈納克與巴特在基督論上的爭論,維真學刊200601期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855
[8]戈爾維策,〈精選本導言〉,K•巴特著,戈爾維策精選,《教會教義學(精選本)》,何亞將、朱雁冰譯(香港:三聯書店,1996),頁xxvii.
[9]林鴻信, 教理史(下), 禮記出版社, 1996, 頁323.
[10]郭鴻標,巴特的生平與神學簡介,http://www.hkci.org.hk/Reflection/No.58/58_theo_sketch.rtf
[11]John C. McDowell,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Our World: Karl Barth’s Socialist Politics Against the Stream. ( Seminar 9) http://scholar.google.com/url?sa=U&q=http://www.geocities.com/johnnymcdowell/edinburgh_lectures/Karl_Barth_in_Conversation_2004-5/Barth_Course_2004-5_Lecture9_Politics.pdf
[12]歐力仁,信仰的類比-巴特神學與詮釋學中的修正與顛覆,香港:文字事務出版社,2004。p.62
[13]同註解10
[14]張賢勇,〈中譯本導言〉,卡爾•巴特著。《羅馬書釋義》。魏育青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頁xxx
[15]歐力仁,信仰的類比,p62
[16]同註10
[17]布爾喬亞(Bourgeois), 就是馬克思口中的資產階級.
[18]歐力仁,信仰的類比,p63
[19]歐力仁,信仰的類比,p63
[20]Barth, letter to Eduard Thurneysen, 5 February, 1915, cited in Jehle,Frank, Ever Against the Stream: The Politics of Karl Barth, 1906-1968,p.28.
[21]James D. Smart,Eduard Thurneysen: Pastor-Theologian,http://theologytoday.ptsem.edu/apr1959/v16-1-article6.htm
[22]The Vernard Eller Collection,Christian Anarchy Chapter 5, Karl Barth, Theology of Christian Anarchy,http://www.hccentral.com/eller12/part5.html
[23]十月革命,是1917年俄國列寧領導下的武裝起義,推翻了俄羅斯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奪權理論的一次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許多國家得到傳播,揭開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序幕,直接導致了蘇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抗。
[24]Eberhard Busch's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Fortress, 1976,p. 106
[25]張賢勇,〈中譯本導言〉,卡爾•巴特著。《羅馬書釋義》。魏育青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頁xxxi
[26]Jehle, Frank, Ever Against the Stream: The Politics of Karl Barth, 1906-1968,p.37
[27]Timothy J. Gorringe, Karl Barth: Against Hegemo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34
[28] 歐力仁,信仰的類比,p.64
[29]巴特著。《羅馬書釋義》。魏育青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頁609。
[30]巴特,《羅馬書釋義》,頁608。
[31]巴特,《羅馬書釋義》,頁607。
[32]巴特,《羅馬書釋義》,頁607。
[33]巴特,《羅馬書釋義》,頁606。
[34]Victor Shepherd,Book review of “Jehle, Frank. Ever Against the Stream: The Politics of Karl Barth”, TorontoJournal of Theology Fall 2003,http://www.victorshepherd.on.ca/Other%20Writings/book_review12.htm
[35]Barth, Action in Waiting for the Kingdom of God, pp. 22f.
[36]Frank D. MacChia :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Liberation : The Message of the Blumhardts in the Light of Wuerttemberg Pietism,Scarecrow Press 1993. p.165
[37]歐力仁,信仰的類比p. 64.
[38]Karl Barth, Der Romerbrief (first edition), 1919, ed. Hermann Schmidt (Zurich: TVZ Verlag,1985), p. 299, cited in Busch, Karl Barth, p. 100.
[39]歐力仁,信仰的類比-巴特神學與詮釋學中的修正與顛覆,香港:文字事務出版社,2004。p.66
[40]巴特,《羅馬書釋義》,頁121 。
[41]張旭,卡爾.巴特神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P.278
[42]Karl Barth, ‘Music for a Guest -- a Radio Broadcast’, in Final Testimonies, reprinted www.religion-online.org/cgi-bin/relsearchd.dll?action=showitem&gotochapter=4&id=420.
[43]Eberhard Bethge, et al.,Dietrich Bonhoeffer: A Biography,Fortress Press. 1998,p.26-27
[44]巴特,《羅馬書釋義》,頁607
[45]此運動為美國信義會牧師法蘭克˙布克曼(Frank Buchman, 1878-1961)在1923年創立之「牛津團契」(Oxford Group)所提倡的。該運動倡導誠實、清潔、無私與愛心四大精神。
[46]Busch, Karl Barth, p. 275.
[47]John C. McDowell,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Our World: Karl Barth’s Socialist Politics Against the Stream. ( Seminar 9) http://scholar.google.com/url?sa=U&q=http://www.geocities.com/johnnymcdowell/edinburgh_lectures/Karl_Barth_in_Conversation_2004-5/Barth_Course_2004-5_Lecture9_Politics.pdf
[48]因為當時瑞士是中立國家,不想捲入戰爭,而巴特的言行造成德國與瑞士關係的緊張。Jehle, Frank, Ever Against the Stream: The Politics of Karl Barth, 1906-1968,p. 42
[49]張旭,卡爾.巴特神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P.282
[50]郭鴻標,巴特的生平與神學簡介,http://www.hkci.org.hk/Reflection/No.58/58_theo_sketch.rtf
[51]Eberhard Busch's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Fortress, 1976,p. 357
[52]Eberhard Busch's Karl Barth,p. 427
[53]Chris Rice,NonIdealogical Politics,book review of "Ever Against the Stream: The Politics of Karl Barth, 1906-1968 by Frank Jehle",Cornerstone Magazine,http://www.cstone.tv/features/2003/January/books.htm#politics
[54]馬克思主義也分成為非革命派與革命派. 非革命派學說, 又稱修正主義派, 以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 為中心, 主張漸進式的社會主義發展, 視馬克思主義為一種道德標準. 而革命派學說則以列寧(Vladimir Lenin) 最為著名, 強調激進強製革命的重要性.兩邊派系皆認為自方學說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55]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1919年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於莫斯科。第一國際即「國際工人聯合會」,1864年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成立,馬克思代表德國工人參加,歷史上稱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即「社會主義國際」,1889年在巴黎開第一次大會,前兩國際均無疾而終。
[56]Karl Barth, ‘The Church Between East and West’, Against the Stream: Shorter Post-War Writings, 1946-1952, trans. Stanley Goodman (London: SCM Press, 1954), 139f., Richard and Martha Burnett’s translation, in Jehle, 88f.
[57]Eberhard Busch's Karl Barth,p. 433
[58]論語子張篇,孔子的學生子張所說的話:“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犯錯誤不可避免,尤其是君子之過,更像日食月食一樣被人看的清楚明白。對於自己的過失,如果他認真的改正了,人們仍會像以前一樣敬仰他。
[59]田立克,《系統神學˙第一卷》,龔書森、尤隆文譯(台南:東南亞神學院,1980),頁6 。
[60]教會教義學(精選本) p. 197-8頁
[61]Jehle, Frank, Ever Against the Stream: The Politics of Karl Barth, 1906-1968,book title.
[62]周偉馳 ,評張旭的《卡爾巴特神學》,人民網,2005年5月,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66/40468/3446467.html
[63]歐力仁,信仰的類比-巴特神學與詮釋學中的修正與顛覆,香港:文字事務出版社,2004。p.121-148無限本質的差異,巴特與哈納克的公開辯論
[64]因為當時瑞士是中立國家,不想捲入戰爭,而巴特的言行造成德國與瑞士關係的緊張
[65]John C. McDowell,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Our World: Karl Barth’s Socialist Politics Against the Stream. ( Seminar 9) http://scholar.google.com/url?sa=U&q=http://www.geocities.com/johnnymcdowell/edinburgh_lectures/Karl_Barth_in_Conversation_2004-5/Barth_Course_2004-5_Lecture9_Politics.pdf
[66]父親 ,臺灣/中國地區,陳映真/著 ,洪範,出版日期:2004,p.142-143
[67]馬太福音7章2-5節
[68]Jehle, Frank, Ever Against the Stream: The Politics of Karl Barth, 1906-1968,p.108
[69]馬太福音5章9節: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